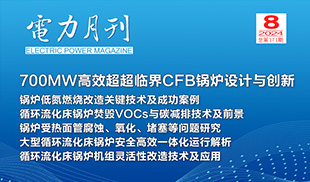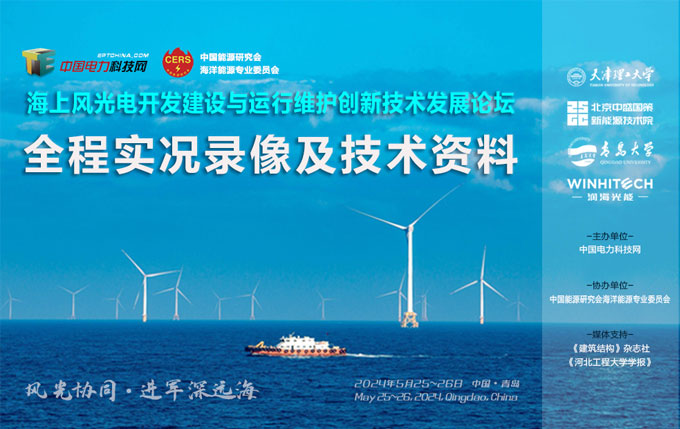碳中和已成全球共識,能源轉型是大勢所趨。碳中和目標下,我國能源結構將發生顛覆性變化,由目前化石能源占比80%以上,轉變為非化石能源占比超80%以上,能源體系也將發生革命性重塑。文章系統分析了我國能源轉型面臨的產業結構偏重、能源結構偏煤、能源利用效率偏低、碳中和窗口期偏短、新能源關鍵礦物供應不足等挑戰,提出在碳中和目標下,我國能源發展應堅持“立足國情、安全發展,科學創新、務求實效”的方針。能源轉型應遵循自主可控和綠色低碳的理念,通過節能與提效雙輪驅動、供給與消費兩端發力,分“三步走”:(1)減煤控油增氣,大力發展新能源;(2)非化石能源加速替代;(3)清潔低碳、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全面建成。系統實施節能、去碳、創新、提效、應急、支撐、合作七大戰略工程,支撐我國如期實現碳達峰、碳中和的目標。
應對氣候變化,實現碳中和是全球大勢、時代命題,關乎人類未來生存發展。2020年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87%,化石能源燃燒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。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(MSCI)發布《MSCI 凈零追蹤》(MSCI Net-Zero Tracker)報告顯示,截至2021年底,全球已有136個國家提出“零碳”或“碳中和”目標,覆蓋全球85%的人口、90%的GDP和88%的碳排放量。中國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參與者、貢獻者和引領者,推動了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》《京都議定書》《巴黎協定》等一系列條約的達成和生效。2020年9月,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宣布:“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,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,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”。碳達峰、碳中和是中央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,將成為中國未來數十年內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基調之一。2021年10月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發布《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》,指出能源綠色低碳發展是實現碳中和的關鍵,能源領域要通過強化能源消費強度和總量雙控、大幅提升能源效率、嚴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費、積極發展非化石能源、深化能源體制機制改革等重大舉措,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,助力國家實現碳達峰、碳中和目標。
1、“雙碳”目標下我國能源轉型發展面臨的挑戰
我國作為全球能源消費和碳排放的第一大國,2020年,一次能源消費量達49.8×108t 標準煤,占全球26.1% ;能源燃燒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為98.9×108t,占全球30.9%。在政策引導和技術進步的推動下,我國能源轉型已取得初步進展,非化石能源消費快速增加,2020年在能源結構中占比15.9%,但仍然面臨產業結構偏重、能源消費偏煤、能源利用效率偏低、碳中和窗口期偏短、新能源關鍵礦物供應不足等一系列挑戰。
1.1產業結構偏重,面臨降能耗與穩制造兩難選擇
目前,我國處于工業化中后期,第二產業占比曾長期處于40%以上,近5年才降至40%以下。2020年,我國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為37.8%,高于制造業強國德國(26.5%,2020年) 和日本(28.7%,2019年),遠高于美國(18.2%,2019年)、英國(17.0%,2020年)、法國(16.4%,2020年),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(27.9%)。我國制造業對GDP的貢獻率為26.2%,比全球平均水平(16.5%)高出近10個百分點。制造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石,夯實實體經濟根基、走制造強國之路必須確保制造業占比穩定。
相對于巴西、澳大利亞等資源國的原料開采和發達國家占據優勢的高端制造業,我國承擔的加工制造環節能源資源消耗強度大、單位GDP碳排放量高。我國第二產業能源消費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70%左右,其中,鋼鐵、水泥、有色金屬、汽車等高耗能產業全球占比高,2020年生產了全球57%的粗鋼、58%的水泥、57%的電解鋁和32.5%的汽車,這是我國能源消耗總量大、單位GDP能源消耗強度高的重要原因。我國制造業整體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,通過調整產業結構降低碳排放強度的難度要遠大于發達國家。
1.2能源結構偏煤,控煤減碳背景下保障能源安全的難度增大
基于我國富煤、油氣不足的資源稟賦,能源消費結構呈煤炭占比大,石油、天然氣、新能源占比小的“一大三小”格局。煤炭長期在我國能源安全戰略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,是我國第一大主體能源。2000年以來,我國煤炭消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快速下降,2020年較2000年下降11.7個百分點,但仍高達56.8%,遠高于全球平均27%和G7國家平均12%的水平。2020年,我國煤炭消費量為39.6×108t,占全球煤炭消費總量的54.3%,是印度煤炭消費量的4.7倍、美國的8.8倍和歐洲的8.9倍。
煤炭具有高碳屬性,其單位熱值碳排放量是石油的1.4倍、天然氣的2倍,煤炭燃燒碳排放占我國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9%,“減煤”被視為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主要舉措。然而,“減煤”速度過快、力度過大,煤炭對能源體系安全運轉的托底保供”作用將會被削弱,短期內會引發能源安全問題,如2021年下半年部分地區由于電煤供應不足引發的“拉閘限電”現象。預計我國煤炭消費量將在“十四五”期間達峰,2035年前仍是我國第一大能源,期間既要控煤減碳,又要發揮好煤炭“壓艙石”作用,保障能源安全的難度越來越大。
1.3能源利用效率偏低,工藝、標準和綜合利用等均有不足
2000年以來,我國單位GDP能耗持續下降,但仍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。根據國際能源署和世界銀行數據,2020年我國每萬美元GDP能耗為3.4t標準煤,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.5倍、美國的2.3倍、德國的2.8倍。分析我國單位能耗偏高、能源利用效率偏低的原因:一是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和高耗能產業占比高;二是部分產業工藝落后,煤炭、鋼鐵等行業落后產能和過剩產能仍然大量存在,部分地方政府仍依賴傳統產業及生產模式維持經濟增長;三是我國能效標準低于發達經濟體,例如歐盟和美國通過提高家電能效標準實現電力消費量下降15%,而我國下降幅度不足5%;四是能源綜合利用率低,據統計,我國約50%的工業能耗沒有被利用,余熱資源利用率只有30%左右,遠低于發達國家40%~60%的平均水平。我國再生資源利用率也遠低于世界發達經濟體。例如,“十三五”期間,我國再生鋁產量占鋁產量的比例為20%,美國達到80%,日本則接近100%。
1.4碳中和窗口期偏短,能源轉型成本高
從碳達峰到實現碳中和,全球平均用時需53年,美國用時需46年,西方發達經濟體平均超過70年,而我國只有30年時間。我國不但要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,還要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,任務艱巨。發達國家的存量煤電資產大多已經進入集中退役期,50%煤電機組平均服役年限在40年左右,部分煤電機組服役年限超過60年。而我國大量燃煤電廠建成服役時間較短,在運煤電機組平均服役時間為12年,約50%的容量在過去10年內投運,85% 的容量在過去20年內投運。按照40年的服役年限,為了實現2060年碳中和,未來新建的煤電機組將在到達壽命周期之前提前退役,擱淺資產損失巨大。根據牛津大學前期研究成果,我國煤電擱淺資產規模可能高達3萬億~7.2萬億元。考慮到近年我國仍在新建煤電機組,實際擱置規模有可能更大。同時,隨著碳中和推進,化石能源需求減少、行業體量縮小、部分生產場地關停成為必然趨勢,傳統資源型城市轉型和相關行業人員分流、再就業等問題也需要統籌考慮。
1.5新能源規模發展面臨挑戰,關鍵礦物供應存在風險
在政策引領和技術進步的推動下,我國核能、水能、風能、太陽能、生物質能和地熱能等非化石能源以及氫能、儲能和新能源汽車產業取得長足進展,但規模化發展仍面臨諸多挑戰。核電部分核心零部件、基礎材料仍依賴進口,核聚變能開發利用尚處于探索階段。水電工程施工環境復雜、生態環境脆弱,工程技術、建設管理和移民安置難度不容小覷。與常規電源相比,風能和太陽能發電具有典型的間歇性、波動性和隨機性特征,高比例新能源條件下電力系統可靠性不足。生物質能發電總裝機容量依然不高,規模化發展仍需時日。地熱能領域干熱巖資源勘探開發技術尚處于起步階段。氫能方面,輸配和典型場景應用成本高,高壓儲氫設備、燃料電池與國外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。儲能方面,抽水儲能發展空間有限,電化學儲能成本高,尚無法滿足長時儲能需求,安全性也有待提高。新能源汽車所需鋰、鈷、鎳等關鍵礦物資源儲量不足,消費量大,嚴重依賴進口,2020年消費量分別占全球的50%、30%、50%,對外依存度分別達到74%、95%、90%,存在供應中斷風險。
2、碳中和目標下我國能源發展戰略構想
2.1總體戰略思想
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“四個革命、一個合作”能源安全新戰略為指引,貫徹落實“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”的新要求,堅持“立足國情、安全發展,科學創新、務求實效”的方針,遵循自主可控和綠色低碳發展理念,通過節能與提效雙輪驅動、供給與消費兩端發力,系統實施節能、去碳、創新、提效、應急、支撐、合作“七大戰略工程”,加速推動能源系統由以煤炭為主的“一大三小”(煤炭大,石油、天然氣和新能源小),向新能源為主的“三小一大”(煤炭、石油和天然氣小,新能源大)轉變,支撐我國如期實現碳達峰、碳中和目標。
2.2第一步(2020—2035年),減煤、控油、增氣,大力發展新能源
通過減煤、控油、增氣,大力發展新能源,2035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占比將超過35%。一是嚴格控制煤炭產量,加大落后產能、小煤礦的淘汰力度,制定老礦合理退出機制,積極推動煤炭深加工產業化示范與規模化發展,全面提升煤炭清潔利用水平。二是加強太陽能、風能、地熱能對化石能源的替代,加快新能源汽車對燃油車的替代,控制石油消費增長。三是加快陸上西部地區天然氣增儲上產,實現陸上東部地區天然氣產量穩中有升,推進海上天然氣勘探開發,持續推動天然氣產業快速發展。四是大力發展風電、光伏,因地制宜規模化配置陸上風電,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大力發展海上風電,積極支持分布式風電、光伏發展。堅持安全第一、生態優先和綠色發展原則,穩步推進水電、核能與生物質能等清潔能源有序發展。五是加快碳捕獲與封存/碳捕獲、利用與封存(CCS/CCUS)技術攻關與示范,推動二氧化碳驅油/氣、化工/生物利用等二氧化碳利用技術及工藝的創新和應用,推進CCS/CCUS國家示范區建設。
2.3第二步(2036—2050年),非化石能源加速替代
強化新能源高效開發利用技術攻關,不斷完善新能源供需體系建設,促進終端用能電氣化水平實現跨越式提升,全面推進新能源產業發展,加快提升新能源消費總量與消費占比,2050年,預計我國非化石能源占比將達到70%以上。一是持續加強節能提效技術、設備的推廣應用,大力推動全社會節能提效,全面實現節能提效預期目標。二是海上天然氣開發取得階段性成果,天然氣儲備、管網體系更加完善,天然氣消費2040年左右達峰后保持基本穩定。三是隨著交通電動化進程加快,石油作為燃料的消費快速下降,作為原料的消費占比快速提升。四是持續推進整裝煤炭開發基地和大型綜合能源化工基地建設,建成以綠色煤炭資源為基礎的精準開發模式,全面提升煤炭兜底保供能力。五是加大CCS/CCUS等環節關鍵技術、工藝、設備的攻關力度,加快推進CCS/CCUS技術在水泥、鋼鐵等重工業領域和天然氣發電領域的規模化應用。
2.4第三步(2051—2060年),現代能源體系全面建成
進一步鞏固風能、太陽能、氫能、核能等清潔能源的主體地位,強化煤炭、天然氣與可再生能源融合發展,以化石能源為主的現代化能源應急儲備體系全面建成,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超過80%。煤炭、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回歸原料屬性,全面推進能源結構綠色低碳轉型。推動CCS/CCUS技術商業化規模應用,不斷完善低碳循環經濟體系建設。全面建成智慧協同、多能互補、多網融合、快速響應的智慧能源系統,我國能源體系綠色低碳轉型取得全面勝利。
3、碳中和目標下我國能源發展的關鍵性戰略舉措
實現碳達峰、碳中和,能源消費結構調整是核心,產業結構調整是關鍵,化石能源清潔化是基礎,節能減排是抓手,建設現代化能源體系是目標。要實施好節能、去碳、創新、提效、應急、支撐、合作“七大戰略工程”,助力“雙碳”目標實現。
3.1節能工程:強化四類節能舉措,推動能源消費實現節約高效
加強意識節能:通過節能理念宣傳、節能硬性約束、黨政機關引領示范等手段,積極引導全社會轉變傳統用能習慣,開展全民節能行動,牢固樹立“節能是第一能源”意識。突出結構節能:通過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節能降碳,加快壓減高耗能產業,嚴格控制增量,調整優化存量,加快推動產業轉型升級,促進我國制造業向中高端邁進。做精技術節能:加強節能降碳科技攻關和示范應用,推進物聯網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與各行業深度融合,依靠技術創新推進行業用能效率提升。做實管理節能:通過節能提效立法,完善節能減排財政稅收優惠政策,強化節能減排監督檢查考核,保障節能減排管理工作持續有效運行。
3.2去碳工程:強化四類減碳舉措,推動能源行業先行碳中和
持續提高工業設備和電力電器能效,加大建筑領域節能降碳關鍵技術創新攻關力度,加快電動車對燃油車的替代,大幅提升工業、建筑、交通等重點行業用能效率和清潔能源消費占比,實現源頭“減碳”。設立碳循環經濟研究專項,加快碳轉化技術研發及應用,加大碳利用產業扶持力度,盡快突破碳循環經濟發展的技術瓶頸和制度障礙,推進二氧化碳化工/生物利用等技術及工藝的創新和應用,實現經濟“用碳”。推動光伏/光熱發電、風電、水電、核電等清潔電力對火電的替代,加強工業領域電力、熱力和氫能應用,構建基于電氣化、光伏建筑、柔性用電系統的新型建筑能源系統,推進交通領域的智能化、數字化、電動化、網聯化和共享化轉型,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,實現有序“替碳”。戰略性開展燃燒前捕集、富氧燃燒捕集等大規模二氧化碳捕集技術研究,集中開展二氧化碳埋存選址理論及關鍵技術攻關,推進二氧化碳驅油/氣、咸水層封存等技術規模化應用,實現科學“埋碳”。
3.3創新工程:突出前沿性、顛覆性技術研發,推動“零碳”能源供應
立足煤炭、油氣、核能、可再生能源、氫能與儲能、智能電網、綜合能源系統七大領域,圍繞基礎研究、關鍵共性技術、前沿引領技術、顛覆性技術、工程示范應用五大方向,系統構建“七橫五縱”技術創新體系。在傳統化石能源領域,不斷發展和推廣煤炭無害化、數字化和智能化開采技術,提高煤炭生產效率,降低煤炭生產端碳排放,同時加強煤炭清潔燃燒和高效發電技術攻關,推動燃煤發電機組靈活高效運行;加大井下油水分離、頁巖油地下原位開采、無水壓裂與增能壓裂等油氣綠色生產技術及新型煉油加工技術攻關,確保油氣基礎供應。在新能源領域,研發可控核聚變能源開發和應用關鍵技術,積極推進熱核聚變實驗堆建設,力爭早日實現“人造太陽”技術應用;大力發展低成本風能、太陽能發電技術,建立基于大數據、云計算、人工智能等的新能源電力智能調控技術,支撐我國沙漠、戈壁、荒漠地區大型風能、太陽能發電基地高效開發和安全運行;大力發展安全高效低成本氫能技術,攻關完善制氫、儲氫、輸氫、用氫技術,統籌推進氫能“制儲輸用”全鏈條發展;大力發展高效率、長壽命、低成本的先進儲能技術,加強全固態電池、鈣鈦礦電池、鋰空氣電池等電池技術攻關,保障新型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。
3.4提效工程:構建靈活可靠的智慧能源系統,推動能效大幅提升
充分應用新一代數字化、智能化信息技術,加快構建“源、網、荷、儲”智慧協同,煤、油、氣、電、氫多能互補,電網、熱網、燃料網多網融合,產、消雙向靈活響應的智慧能源系統,實現多種能源系統在供給側、輸/配側、需求側的互聯互通與深度融合。支持和鼓勵各類能源主體自主接入能源系統,雙向參與能源市場交易,促進能源利用效率和服務水平大幅提升。
3.5應急工程:構建扎實穩固的應急儲備系統,確保能源安全自主可控
通過實施綠色煤炭資源勘探開發重大科技創新工程,集中建設整裝煤炭開發基地和大型綜合能源化工基地,保留必要的產能儲備等措施,做好煤炭兜底保障能力建設。長期維持煤電裝機容量(2.0 ~ 4.5)×108kW,使電力安全供應天數保持在90天的安全閾值水平上。構建兼具保底和調節功能的石油儲備體系,儲備規模達到120天進口量水平,實施“探而不采、產能儲備”戰略,建立10×108t 探明地質儲量規模的石油資源戰略儲備。突出天然氣與新能源“最佳伙伴”關系,強化天然氣儲備,盡快建成一定規模的國家天然氣戰略儲備,形成包括國家、地區、企業三級儲備主體,戰略儲備和商業儲備相結合的天然氣儲備體系,逐步增加儲氣規模,形成地下與地上相結合的儲庫系統。
3.6支撐工程:建立與時俱進的配套政策體系,保障能源安全轉型
統籌制定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協調發展政策,建立健全化石能源企業轉型、退出機制,制訂可再生能源發展專項規劃。按照“先立后破、破立并舉、等量替代”的原則,充分利用傳統能源資源地區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的優勢,做好接續產業的區域轉移和承接,特別是做好重化工行業、大型數據中心等高耗能產業在中西部能源資源富集地區的布局,形成產業接續與可再生能源就地消納的雙贏格局。加大科技創新支持力度,設立并實施戰略性科技重大專項,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,集中優勢資源,構建國家碳中和戰略科技力量體系,打好碳中和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。堅持“全國一盤棋”和“共同但有區別原則”,充分考慮各地區差異,科學合理分配碳排放指標,完善碳排放“雙控”制度。盡快建立自主碳排放計量體系,加強溫室氣體排放、碳核查等領域基礎數據采集;持續深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,探索建立綠色金融改革實驗區。
3.7合作工程:充分利用兩個市場、兩種資源,推進綠色能源國際合作
堅持全方位國際合作不動搖,落實“一帶一路”倡議,持續打造開放條件下油氣安全保障體系,高度重視中東、中亞—俄羅斯地區低成本、低碳足跡油氣資源項目獲取,加強天然氣和LNG領域國際合作。推進能源產業國際化,建立新能源國際合作運行及投資體系,鼓勵先進新能源技術在“一帶一路”國際市場中的應用和推廣,提高新能源國際合作水平。發揮我國新能源關鍵礦物產業鏈和技術兩大優勢,在共建“一帶一路”框架內,促進新能源關鍵礦物領域的對話交流與合作,打造供應國、通道國、消費國一體化協同保障的供應鏈體系,構建原礦、精礦、產品多類型進口機制,最大限度降低供應風險。積極在國際合作內容、機制、途徑、對象等方面進行創新和實踐,在能源安全新戰略的指引下,加強與先進發達國家在煤炭清潔化利用、甲烷減排、先進核能、CCS/CCUS等綠色低碳技術領域的合作,加強與鄰國電力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。
4、結束語
在碳中和目標指引下,我國作為全球主要的能源消費國與二氧化碳排放國,未來能源轉型面臨經濟、技術、安全、社會等多方面的壓力和挑戰,能源行業需加強規劃,突出重點,扭住關鍵,精準發力,狠抓落實,加速化石能源與新能源融合發展,加快建設以化石能源兜底、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清潔低碳、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體系,為國家如期實現碳達峰、碳中和不斷做出新貢獻。